《山脊》 小说介绍
山村沙漠的这部小说《山脊》十分精彩,反转永远在你想象不到的地方,主角贺松英子形象塑造得非常成功,第四章最穷人家介绍:“行了行了,脱贫是硬任务,完不成不行。村委五个人,每人包两个组。贺副主任,你就包刘阳洼和顾记山。”赵俊成磕了磕烟锅。“行!支......
《山脊》 第四章 最穷人家 在线试读
“行了行了,脱贫是硬任务,完不成不行。村委五个人,每人包两个组。贺副主任,你就包刘阳洼和顾记山。”赵俊成磕了磕烟锅。
“行!支书,出山的路该修了。”贺松略略提高了声音。
“早该修了,可是……唉……”
“贺副主任,村上乡上都想修,可就是没钱。你们水利局有钱单位,给咱支持点资金?”耿福昌马上换成了笑脸。
“刘主任,会支持的。只是我刚来……支书,要是再没其他事,我想去包扶的庄子上。”贺松站了起来。
刚来就要钱,还跟自己唱反调,他很不舒服。
“也行,强文陪着去。”
“两个庄子都不远,骑摩托还是步行?”三十多岁、魁梧结实的文书强文问。
“步行吧,我想多看看。”贺松背起了背包。
“我也去。”妇联主任孙小琴提起了包包。
三个人漫步在田间小道,边看边畅谈着。
“贺副主任,刘阳洼和顾记山可是全村、甚至是全乡最烂的两个组,平时连会都开不起来,要想脱贫,难啊!”强文望着晴空。
“支书看贺副主任是水利局下来的,就把最难搞的组给了贺副主任。还有耿主任,也太那个了……”二十七八岁、丰满结实的孙小琴捡起土块扔了出去。
“下来就是干活的,不怕烂,咱当兵的专啃硬骨头。”贺松望着两侧干涸的土地。
“贺副主任,你也看见了,咱这地方,山大沟深,除了种地再也干不成个啥。就这种地也是十年九旱,先祖们种了一辈子地都没吃饱过几年肚子。”强文感叹道。
“强哥,我倒觉得挺不错的。你看这蓝的天,干净的空气,还有没有任何污染的土地……现在人追求的不就是这个吗?”贺松夸张的呼吸着。
“没看出来,咱贺副主任还是个文人。”孙小琴笑道。
“念过几天书,大部分又还给老师了。要是把大山都变成绿色,再能有水,咱这就是金子都不换的好地方。”贺松畅想着。
“那都是梦啊!那些山光秃秃的,可谁都不愿种树。咱村今年给了三千亩造林,到现在一亩都没人要。”强文苦笑着。
“为啥啊?”
“都想放羊呗!”
“放羊?就那些秃山?”
“那是刘阳洼的队长。”孙小琴叫道。
贺松扭头一看,不远处锄地的,正是刘贵仁大叔,便大步走了过去。
得知贺松跟刘贵仁是老熟人,强文和孙小琴说笑了一会就回了村部,贺松也跟着刘贵仁回了刘阳洼。
刘贵仁院子很大,挖了好几孔大窑洞。只是偌大的窑洞里空空荡荡,没有一件像样的家具。
“实在不好意思,没个像样的凳子。”刘贵仁苦笑着。
“叔,您是全村乃至全乡最富有裕的家庭。双老健在,儿子硕士,女儿重点大学,这精神财富再有钱也不一定拥有。”贺松坐在炕沿上。
“就是,等我和哥工作了,一定要让爷爷奶奶和爹娘过上好日子。”英子递给贺松一杯开水。
“还是咱英子出息。”贺松望着英子,不由得暗暗感叹。
昨天光看这丫头可爱,没想到今天一身素颜,却是无比的清纯美丽。那些什么明星,简直没法比。
“主任,我叫人开会?”刘贵仁点着了烟锅。
“先不急。您带我到庄里转转,去看看最穷的,再看看最难缠的。”
“那好吧!”
刘阳洼三十多户人,绕山而居,相当分散。
走进一户人家,贺松眼泪差点都出来了。
这户人家院墙坍塌的不成样子,连个大门都没有。窑洞顶上裂开几道缝,若不是用椽子顶着,就得塌下来。
见贺松和刘贵仁进来,一个五十多岁的大叔从炕沿上挪下来。炕上躺个老人,瘦骨伶仃。
“大爹,村上贺主任来看您了。”刘贵仁从挎包掏出一包糕点给老人喂着。
“哦,坐……”老人气息微弱,干枯的手指抬了抬。
“主任,这是我的本家哥哥,俩口都有病,干不了重活。他老爹八十多了,在炕上瘫了八年。”
“那……他们咋生活?”贺松还没从震惊中反应过来。
“全靠两个儿子外面打工。一个三十多了,一个也快三十,都没成家,挣的钱大都买药了,唉……”
“不是有医保吗?”
“幸亏有医保,不然……可医保又不是全报。贵成哥,这个月给你寄钱了吗?”刘贵仁扭头问。
“还没呢……”刘贵成蹲在地上。
贺松见窑洞后面是锅台,就走了过去。揭开锅一看,里面有一些黄米饭,却没有任何菜,更没有一点荤腥。
“大叔,你们就吃这?”
“嗯呐……”
“有低保吗?”
“没的……”
“为啥啊?”贺松提高了声音。
“我俩娃在外面打工。”
“叔,你有低保吗?”贺松转身问刘贵仁。
“我倒是有,都给贵成哥了。虽然没几个钱,对这家也能顶大事。”
“大叔,给!”贺松掏出几百块钱塞到刘贵成手里。
“主任,这……”
“叔,走吧!”贺松转身走出了屋子。他啥都说不出来,只觉得心里堵,几乎喘不过气来。
“咱组这样的人家还有不少,要不咋能是全乡最穷的组?不过,最可怜的就是这家了。走,咱再进一户。”
走进另一户人家,贺松满腔的怒火。
这户人家院里堆满了垃圾,屋里又脏又臭,地面居然高低不平。
一位七旬老奶奶坐在炕上,神情痴呆,手上脸上满是污垢。后面的锅台肮脏不堪,有几只碗里长了绿毛。
“这家再没人吗?”贺松头发都要竖起来了。
“这是我堂婶,腿脚不好,眼神也不好。有两个儿子,老人跟小儿子过。”
“小儿子呢?”
“有几年没回来了,也不知去了哪。”
“大儿子呢?”
“就在旁边。”
“走,去大儿子家。”
砖砌的院墙,朱红的大门,宽敞整洁的院子,坐落一排高大的瓦房,无不显示出主人的勤劳和精明。
这样的光景,这样的人家,必须得赞誉。
可贺松却没有任何兴奋,黑着脸走进了屋子。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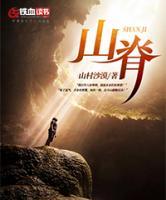 山脊
山脊
 帝后叶辰洛红颜
帝后叶辰洛红颜 猪肚鸡汤
猪肚鸡汤 绝美女帝洛红颜选帝后
绝美女帝洛红颜选帝后 末日降临,先杀同事
末日降临,先杀同事 林筱兰慕棋川
林筱兰慕棋川 反杀狠毒白眼狼
反杀狠毒白眼狼 命硬的长嫂
命硬的长嫂 千万别用一次性四件套!
千万别用一次性四件套! 为陪女兄弟旅游,男朋友假装跟我分手
为陪女兄弟旅游,男朋友假装跟我分手 顾时薇胤辞
顾时薇胤辞 长叹雁归难留全文在线阅读
长叹雁归难留全文在线阅读 姜妩
姜妩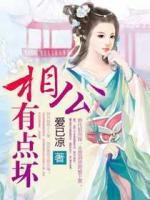 相公有点坏
相公有点坏 恶魔宝宝:敢惹我妈咪试试!
恶魔宝宝:敢惹我妈咪试试! 法医狂妃:王爷你好毒
法医狂妃:王爷你好毒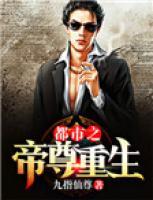 都市之帝尊重生
都市之帝尊重生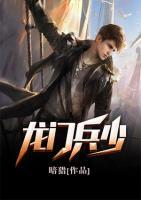 龙门兵少
龙门兵少 娇养小厨娘
娇养小厨娘 陆先生,余生多指教
陆先生,余生多指教 厉总追妻套路深
厉总追妻套路深 总裁男神恋上我
总裁男神恋上我 先婚后爱:总裁老公好嚣张
先婚后爱:总裁老公好嚣张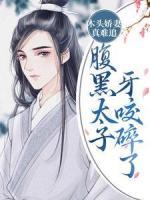 木头娇妻真难追!腹黑太子牙咬碎了
木头娇妻真难追!腹黑太子牙咬碎了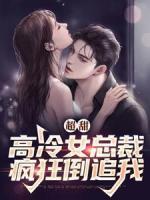 超甜:高冷女总裁疯狂倒追我
超甜:高冷女总裁疯狂倒追我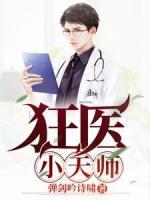 狂医小天师
狂医小天师 柳暗花明
柳暗花明 妹妹抢夫君,假千金她种田去了
妹妹抢夫君,假千金她种田去了 心照不宣
心照不宣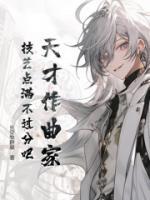 天才作曲家:技艺点满不过分吧?
天才作曲家:技艺点满不过分吧? 狱中归来:邪医仙
狱中归来:邪医仙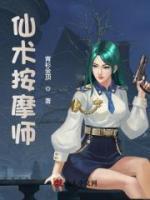 潜龙入海
潜龙入海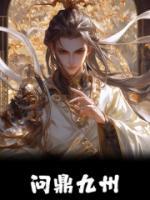 问鼎九州
问鼎九州